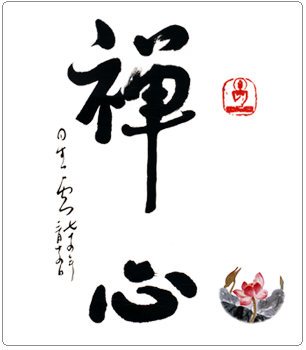為了「說禪」,不得不談一段「古」。話說五十多年前,編者有緣往廣東乳源雲門寺親近禪門泰斗虛雲老和尚;稍後又到過揚州高旻寺,鎮江金山寺入「禪堂」、「聽開示」、「參話頭」……坐在蒲團上提起念頭來冥思默想:「我是誰?」「誰是我?」疑念未斷,參來參去參不透,仍在黑漆桶內打圈圈,到頭來:「我還是我!」始終未能找到「本來面目」。而今在鵬城重遇恩師本煥上人,一代高僧,契機施教,語多鞭策,當頭棒喝:「百尺竿頭,再進一步!」箇中乾坤,破除妄念,繼找「話頭」。參!
究竟「禪」是甚麼!它甚麼都是,但是,甚麼都不是。
禪,不可說,但是,又非說不可!由於禪的宗旨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所以大多數的人,只要一談到禪,總認為那是非常抽象且深奧的。其實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無一不含有禪機,因之,禪是不能離開生活,離開生活便沒有禪。《覺悟的智慧》、《歡喜的智慧》、《自在的智慧》裏面講的是習禪的方法。這些方法因人施教,靈活多變,生動活潑,新穎卓異,能迅速有效地啟發人「開悟」,是歷代禪宗大師卓越的創造,宛如顆顆璀燦的明珠,閃爍著智慧的光芒!歷代禪師的每段公案、語錄、機鋒,皆能盪滌世人的塵勞,導引人們掙脫生活的桎梏,得大自在!進而啜飲生命無盡的泉源,跨入永恒的彼岸,超脫「生死輪迴」之苦,是人生追求的終極幸福。
不立文字
佛家「禪宗」一個根本宗旨是:「不立文字」。
說起「不立文字」,恐怕很多人不易理解,或許也有不少人難於接受。一般人,都把語言文字看為是溝通的工具,離開它,又怎能表達相互之間的思想感情呢?
語言文字,在人們生活中必不可缺少的,比如說,談情說愛,是離不開語言文字傳達愛情的手段,離開它,又該如何表達呢?如果深一層去想,當一對戀人情意綿綿時,到了這一境地,語言文字作用,似乎又嫌累贅了。
所謂「禪境」也者,與此頗有相似之處。應該懂得,語言文字有一定的局限性,甚至會弄巧成拙,把本來很清楚的事物,越說越糊塗,甚至離題千里。
禪,不靠語言文字,倒是要靠人去思維,去想,去猜,去疑;禪師們常用的一句話:「我是誰?」「誰是我?」要找出一個究竟來,怎樣找法?就是要自己苦思冥想,思不透,想不通,還得再找下去!內心思潮,翻騰不息。詩人說,「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禪宗不須文字、語言。但它卻要一個「疑」字,所謂「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有了悟境,就不同尋常了。
禪是甚麼
說到「禪」字,人們便會想起,它是佛家的!如果這樣認為,這是「死禪」,而不是「活禪」。應該說,禪,是人人具備的;凡是人,都與禪掛得起。沒有禪性的人,活著是短暫的,生命是黯淡的;有了禪性的人,才能把握住真實生活,並使生命散發出永恒的光輝。因此之故,人人都在追求「禪」了!
不可否認,從歷史角度來說,發掘「禪」的真理的人,是佛家始祖釋迦牟尼。
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釋迦牟尼講經說法四十多年,在說到最高、最奧妙境界時,他順手拈起一朵花示意,在座聞法的諸大弟子面面相覷;唯獨摩訶迦葉尊者微笑會意,心心相印,契悟真諦。於是釋迦牟尼便將「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道傳給了他,禪——就這樣在拈花微笑間產生了。
由禪達到的境界,不是靠文字、語言所能表達出來的,它太不可思議了;文字、語言有一定的限度,怎麼說也說不清楚。有一位禪師說:「禪是大海,是空氣,是高山,是雷鳴與閃電。是春花,是冬雪。不,它在這一切之上,它就是人。」
他說這一番話,誰又能理解到多少呢?
一默如雷
世間上任何東西,無論是山河大地,抑或是樹林花草,都是藉由其自身的特點來表明,它們的存在是具有真實性,人人都能看到、接觸到的。也因此才有詩、歌、晝等的產生。
由此可見,人類的感受,來自實物的體驗,而語言的傳達,不是絕對的重要。花開花落,也是自然界普遍的現象。但在詩人、畫家的眼裏,在心目中別有一番滋味了。正如一位大師所說:「一默如雷」一樣。沉默,卻猶如雷鳴般地震耳!
實際上,沉默並非無聲,而仍有真實的聲音,只因音階不同,一般人聽不到罷了。所以必須有實際的經驗,才能領略到無言的聲響。
從前,有一位修行者到深山拜訪禪師,請求指點。
閉目靜坐的老禪師卻避而不答,反問道:
「你到這裏之前,是否曾經過山谷?」
「是的,我曾經過一個山谷。」
「你可聽到山谷的聲音?」
「聽到了!」
「那麼,從聽到山谷聲音的地方進去,就是通往禪門之路了。」聽山谷聲是禪的第一步。
詩有禪味
有一首古詩,很有意境,禪味十足:
「竹影掃階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
一座古剎四周,翠綠竹林,月夜清風,佛殿階前竹影搖曳不已,宛如掃帚掃地一樣。事實上,只是影子在晃動,自然掃不動台階的塵埃。
同樣的,月光雖然照透深潭,但潭底也不會留有痕跡啊!這兩句詩,充分地顯示了忘我而意態悠閑的情境,換句話說,不受任何東西的感染,一舉一動好像風景一樣,自然而純真,絲毫沒有滲假造作,本來如此。
「水流任急境常靜,花落雖頻意自閑。」任何人能經常保持這樣的心境,來處事接物的話,身心是多麼地自由自在,無憂無慮,無牽無掛啊!
「詩為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
不論是寫詩或詠詩,在思想、感情上都有一種超現實的境界,不受外界的束縛;而寫出來的詩具有「言有盡而意無窮」、「言在此,意在彼。」而禪師的︽語錄︾記載,亦近乎詩的格調,往往藉「有限表無限,具體表抽象,特殊表普遍」的表達方式,以進入「海闊天空任邀遊」的禪境中去。
辣椒煮魚
佛印禪師與蘇東坡大學士交情甚篤,趣味相投。
有一日,蘇軾在東坡草堂裏煮了一尾大鯉魚,正待食用。忽然家人報稱:佛印和尚來了。東坡便吩咐家人說:「快快把魚藏起來,免得他吃魚犯戒律啊!」
於是家人把那一盤魚藏在天花板上,草簷之下,那是誰也料想不到的。
佛印禪師剛坐下,突然聞到一股辣椒煮魚的味道來,又看不到桌上有魚。心中好奇,他張目四望,發現天花板下有些異樣,他想,魚藏在那裏了,便故意問道:「學士的尊姓,究竟是怎樣寫法呢?」
「奇怪,你明知故問,難道你也不知道蘇字寫法嗎?。」
「我當然知道,只是有人把魚字放在左邊,而將禾字寫在右邊,也有剛剛相反的,那也是一個蘇字嗎?」
東坡立即回答說:「那只是一個俗字而已。」佛印又問:「最近還看見有人寫蘇字,把魚放在草字之下,禾字之上,是不是也可以呢?」
「那卻是不可以的!」東坡回答說,卻有點疑惑不解的樣子。
「既然不可以,就應該從草簷之下,木板之上,拿了出來嘛!」這時,大學士才「悟」了過來,心想,誰也逃不過他的慧眼啊!
放屁放屁
能進入「禪境」的人,自然而然有一種「定力」;所謂「定力」也有程度上的差異,這是取決於習禪的功夫深淺了;沒有具足「定力」的人,純屬浮誇。一試,就原形畢露,不攻自破。
宋代大學士蘇東坡是一典型例子。有一日,他寫了一首五言絕句說:
「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
他自認為自己禪境高,到達了「八風」吹不動的境界了,越想越得意,大有飄飄然之感!
蘇東坡叫書僮將這首詩送給好友廬山歸宗寺佛印禪師去過目,希望這位禪師好好稱讚他一番。
佛印禪師看了之後,在原詩箋上草草寫了幾個字,套上信封,要書僮帶回去。蘇學士拆閱一看,勃然大怒,拍案大罵說:「豈有此理,出家人怎麼如此之無禮!」
佛印禪師在原詩箋上,只是寫上「放屁,放屁!」四個大字而已。蘚學士氣沖沖趕往歸宗寺去,過了江,直闖方丈室興師問罪。剛抵門外,忽見禪門上貼上一幅聯語,寫道:
「八風吹不動,一屁過江來。」
所謂「八風」:即「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凡是有「定力」的人,不會被這些外境所困惱。
延年益壽
習禪的人,功夫深,有了「禪定」境界,就能延年益壽。近代高僧虛雲老禪師,活了一百廿多歲,平時到處講經說法,思維清晰,健步如飛,還能登高爬山,挑土擔泥!
凡是進入「禪境」的入,情況都相似;尤其僧入,生活淡泊,青菜蘿卜,粗茶淡飯,日子過得寧靜、舒暢、煩惱少。相反的,那些貪圖「口福」的人,餐餐山珍海味,看來營養極其豐富,事實上並未見得延年益壽。
台灣一位學者做了一份調查:有生卒可考的僧尼五百七十一人,其中百歲以上者十二人,九十歲以上者四十二人,八十歲以上者一百四十二人。七十歲以上者三百六十一人,佔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三點七。六十五歲以上者四百三十三人,佔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五點八。
與歷代帝王比較,高僧長壽者所佔百分比,要高出帝王十倍以上。即以六十五歲以上者所佔百分之七十五點八的比例來說,也要比現代西方發達國家六十五歲以上的人佔百分之十五點六的比率,高出四或五倍哩!
僧尼們多長壽的原因,與他(她)們的生活方式、飲食習慣、心理狀態等條件是有關係的。但主要得益於「坐禪」,這是毫無疑問的。
放下屠刀
有一位禪師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這句警語足以使人深思!自古至今,能有多少人對「名」、「利」、「權」看得淡薄呢?又有幾許人放得下呢?
正由於「放不下」,煩惱多多,為了盲目追求目的物,甚至不擇手段,挖空心思,絞盡腦汁,旨在必得,得不到呢?昧著良知良能,做盡壞事!人間悲劇,層出不窮。
「放下屠刀」也者,就是勸告愚昧者,不可繼續作惡,如果能放下,不做懷事,一心向善,這個人,就是佛了。可是,人的私慾貪念,是無止境的,欲阻止這種貪念,徹底放下,談何容易啊!
過去,有一個修行的人,請問趙州和尚說道:「我已拋棄一切,兩手空空,又該怎麼辦呢?」
趙州和尚回答:「放下吧!」這個修行人疑惑不解地說:「大師呀,我已兩手空空了,還有甚麼東西可放下呢?」
趙州和尚回答說:「那麼,再把一切挑起來吧!」、世間上的東西,好似沉重的包袱一樣,放下來,捨不得感到痛苦!既放下,又重新挑起來,豈不是更痛苦?試問,到底是放下好呢?。還是挑起來好呢?
沒有功德
「禪」的最高境界,是不「著相」;凡是「著相」的人,就離「禪」的境界太遠了。可是,世間上「著相」的人比比皆是,要他放棄「相」的觀念,太難了。所謂「相」,是一切事物的實體,誰能離得開它呢?凡是「著相」的人,很難進入「禪」的最高境界。
當年,禪宗初祖達摩禪師來到中國,與梁武帝會晤一席話,就是典型的例子。
這位信佛虔誠的皇帝,見到達摩禪師問道:「自我登位以來,建了不少廟,印了不少經,供養了不少和尚,是否有很大的功德呢?」。達摩回答說:「沒有。」
梁武帝奇怪地又問道:「為甚麼沒有呢?。」達摩回答說:「因為你所做的只是一點世俗的小果報而已,談不上真功德。」
梁武帝又問:「那麼,甚麼才是真功德呢?」
達摩回答說:「真功德是最圓融純淨的智慧,它的本體是空寂的,你不可能用世俗的方法去得到它!」
達摩發現梁武帝和他沒有緣分,便往嵩山少林寺去了。
由此例看來,梁武帝太「著相」了,一切煩惱,皆由執著而來,滿腦子執著「相」。試問,放不下「包袱」,怎能參禪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