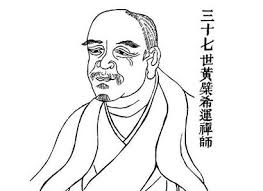
【六祖下第四世】
洪州黃檗希運禪師(~ 八五五)姓氏不詳,福州閩縣人也。幼於本州黃檗山出家,後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
洪州黃檗希運禪師(~ 八五五)姓氏不詳,福州閩縣人也。百丈禪師公案講完,接著看下一位,六祖下第四世洪州黃檗希運禪師。洪州就是江西省的南昌,黃檗是山的名字 叫黃檗山,希運是黃檗禪師的法號。黃檗禪師這個人高深莫測,他什麼時候出生的居然沒有人知道,當然有一種說法是說他出生在西元七百七十六年,但是大部分的資料都查不到,而他圓寂於西元八百五十五年。為什麼大家說他高深莫測?你看,他姓氏不詳,連他的俗姓都沒有人知道。你知道為什麼沒有人知道嗎?比如有一天你出家了,我們都是出家人,然後我現在問你,我俗姓姓王,仁者,你俗姓貴姓?「俗姓姓陳。」你看看,你看我好相處還是不好相處?「好相處。」所以我都關心你姓什麼?你多少歲?你娶了沒有?幾個孩子?你為什麼不要娶?你們都這樣關心人家對不對?你們的慈悲都是那樣,這是好奇心,人家來,就是很好奇的一直問一直問。那為什麼黃檗禪師他出家那麼久,沒有人知道他姓什麼?就代表他有沒有說?「沒有說。」你現在去哪裡找這種修行人?也就是說,他一心向道,他不跟別人談這些事情,所以大家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出生的,連他的俗姓都不知道,只知道他是福州閩縣人也,跟他師父百丈禪師一樣,都是福建省的人。
幼於本州黃檗山出家,後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黃檗禪師自幼就在黃檗山出家,出家一段時間之後,自己已有一定的程度,程度到達多高,我們看後面就會知道。假設自己沒有一定的程度,怎麼去參訪?我們現在的人自己沒有程度,然後就要去參訪,那是錯的。那是亂跑道場,自己要有一定的程度才可以出去參訪。黃檗禪師後來遊歷到天台山的時候,遇到一位出家人,與那個出家人相談甚歡,就好像是已經認識很久的同參道友一樣。
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熟」就是仔細的意思,黃檗禪師仔細看這位出家人,看到他目光炯炯有神。我們看一個人,其實我們第一眼就是要看他的眼神。其實你也可以看到,只要是成功的人,有成就的人,目標很明確的人,道心很堅定的人,他的眼神都很好。你要看這個人跟一般人一樣不一樣,你看他的眼神就會知道。從近處看,你可以看到他現在的狀態,從遠處看,你也可以看到這個人以後一定有成就。有一句話講:「眼睛是靈魂之窗!」所以,這個人修得怎麼樣?就直接看眼神。黃檗禪師一看到這個人,知道他是個有修行的人,「乃偕行」,所以才跟他同行。
看這些禪師,他們所展現出來的,跟我們的想法是不一樣的。就像我們讀《法華經》,那些大菩薩遇到其他人,不見得會為他們講法,也不見得會跟他們住在一起,《法華經》安樂行品不是有這一段嗎?那為什麼是這個樣子呢?因為因緣未到,不是同參道友。黃檗禪師自己程度很好,他看到這個僧人,知道他是個很有修行的人,因為兩個人相談甚歡,所以就一起遊行。
屬澗水暴漲,捐笠植杖而止。這個「屬」就是連接,山跟山連接的地方就叫做「屬」,「屬澗水暴漲」就是山澗當中河水暴漲。「捐」是「棄」的意思,這個「笠」是竹笠,就是我們所講的斗笠,所以「捐笠」的意思按照文字的解釋,就是把斗笠丟掉,但是如果按照一般的解釋,就是將斗笠拿起來,可能拿起來掛在背後。「植杖而止」,「植」就是依靠,那個「杖」,以前的出家人都有禪杖,地藏菩薩手上拿的那一支叫禪杖,以前的出家人他們出門遠遊都帶一支禪杖,一則可以防身,二則可以打草驚蛇,才不會踩踏到地上的蟲獸,三則可以當枴杖保護自己。「屬澗水暴漲捐笠植杖而止」,遇到山裡面的河水暴漲,就撐著禪杖站在那裡。
其僧率師同渡,河水暴漲了,那個出家人約黃檗禪師說,來吧,我們一起渡河。
師曰:兄要渡自渡,如果是我們就不會像黃檗禪師這樣講話,我們一定會怎麼講?「不要啦!很危險!」我們會講什麼,我們自己跟別人大概都可以猜得到。所以所有的戲劇,它劇本怎麼寫,劇情後來怎麼發展,其實你本身都可以當導演,因為你都知道,不管你是看現代戲,看古裝戲,都一樣。接下來他會生氣,他會罵他,他會摔茶杯,他要去撞墻,其實你們都可以事先猜到。我有說錯嗎?你們電視劇看久了,你們都知道下一幕要演什麼?因為那導演沒開悟,腦袋都和我們一樣,所以我們都猜得到。但是猜得到你別高興,因為代表你也沒開悟,那個情節都讓你猜對了,還有什麼好看的,那為什麼要看?因為就是沒有活在當下,無聊,所以亂看。黃檗禪師就說:「要渡你自己渡啊!」
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那個「褰」字念「千」,意思就是提起,那個「躡」就是踩,也就是那位出家人就將他身上所著的長衫拉高,然後直接踩著水面,就像在踩平地一樣這樣直接過河去了。
你看到電影沒有?你有沒有看到電影的那一幕?好像是達摩一葦渡江一樣。達摩一葦渡江,達摩還需要踩一個東西,他連踩都不用,這樣就走過去了。那你知道這個人是什麼人吧。如果你跟這樣的人遇在一起,你高不高興?你會覺得你是何其有幸,何其的榮幸啊!對不對?就像悟達國師到後來不是遇到一個阿羅漢嗎?最後那個阿羅漢教他用慈悲三昧水來治他膝上的人面瘡。
回顧曰:「渡來!渡來」這位僧人是一個阿羅漢,他渡河之後,回過頭來就跟黃檗禪師講說:「渡來!渡來!」你過來啦!
師曰:「咄!這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啊!嚇死人了!你敢罵阿羅漢嗎?你一定跪下來拜,跪著向他磕頭,你還敢罵他呢?那你知道黃檗禪師什麼人了吧!我們一般人會求神通,求感應,今天已經有一個人在你面前展現這樣的功夫了。那麼像我們一般人,我們會覺得很羨慕,求之不得,我們會說:「我什麼時候才能達到這種境界呀?」我們會從這個角度來想。但黃檗禪師他不這樣看,修行不是為了神通,所以黃檗禪師當下就罵他:「你這個自了漢!」也就是說你是個獨善其身的人!黃檗禪師說:「吾早知當斫汝脛。」就是說如果我遇到你,早知道你會這樣,「當斫」那個「斫」就是砍,「脛」就是小腿,我早知道你會這個樣子,我就把你的腿砍下來。你羨慕神通嗎?你的心量到什麼程度人家一看就知道。但黃檗禪師的心量,「其僧歎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
我們看到這一幕一般我們就會想,這個人一定是佛菩薩化身來考驗他,考驗他是什麼根器的人。我們學佛最主要是要學一佛乘,不是要學神通。當然,這個阿羅漢是什麼來歷我們不知道,我們只能說,這個阿羅漢其實是來考驗他的,但我們也可以說黃檗禪師的程度真是很高。
師後遊京師,因人啟發,乃往參百丈。丈問:「巍巍堂堂,從何方來?」師曰:「巍巍堂堂,從嶺南來。」丈曰:「巍巍堂堂,當為何事?」師曰:「巍巍堂堂,不為別事。」便禮拜。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丈良久。師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丈曰:「將謂汝是個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曰:「某甲特來。」丈曰:「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
師後遊京師,因人啟發,乃往參百丈。一個行者,不論開悟前,還是開悟後,就像趙州禪師,他開悟後八十歲時他還繼續行腳,還繼續參訪。那當然黃檗禪師的程度也很好,但他也還要繼續參訪。之前講過,他跟一位阿羅漢同遊天台山,現在他自己獨自到了京師,他到京城,就有人跟他說:「你應該去參訪百丈禪師。」在黃檗禪師那個時代,百丈禪師是一個很有名的禪師,所以他就到百丈山去參訪。
丈問:「巍巍堂堂,從何方來?」師曰:「巍巍堂堂,從嶺南來。」百丈禪師是一個開悟的禪師,他一看到黃檗禪師,他用這句話來形容黃檗禪師「巍巍堂堂!」意思就是說「你是一個道德很崇高的修行者。」我們現在一般人不會這樣形容,我們現在會說:「啊!法師,你看起來很莊嚴!」或是說:「唉呀!法師,你看起來很有修行。」你們也不習慣於讚美別人,縱使你們讚美別人也是很含蓄,你不敢很肯定的說:「哇!你是一個什麼?」「我看你就知道你是一個很有志氣,很有道心的修行者!」我們很少有人會這樣去讚歎別人。尤其我們會掉入一個陷阱,好像是來請教我的,程度一定比我差。比如我現在到其它寺院參訪,我去參訪人家,人家第一個概念,好像說「你是不懂,所以你來參訪。」不要掉入這個陷阱,不要以為問你問題的人,程度一定比你差。年紀比你輕的,資歷比你淺的,或是你的後生晚輩,不一定程度比你差。
當別人讚美我們的時候,我們應該怎麼回應呢?你看黃檗禪師怎麼回應。百丈禪師問說:「有志向的修行者,你從哪裡來?」黃檗禪師接過百丈禪師的話:「巍巍堂堂,從嶺南來。」他全然接受!你會這樣回答嗎?「嶺南」就是曹溪。我有時會到處參訪,我去參訪的人,有些也是唯唯諾諾,表面上好像是客氣、謙卑,其實根本是心虛。謙卑和心虛要分清楚。但是參訪到後來,我覺得,當我們自己也不敢承擔,不能肯定,那你要去跟人家參訪什麼呢?所以到後來我去參訪,當別人問我說「你從哪裡來?」我都直接跟對方說:「從曹溪來。」就有法師問我說:「曹溪是桃園大溪的附近嗎?」如果聽到這樣的話,我就說:「我要回桃園。」但是絕大部分的法師都知道曹溪的意涵,所以當我說我從曹溪來,一般問我的人話就講不下去,為什麼?因為沒有幾個人敢這麼說。我講的是真話哦!我講的是真話!我不是講我從禪心學苑來,因為我是來跟你請法,我表明我是學曹溪的禪法,我很清楚的表明這個意思,並不是說我有什麼程度,或是說我很高傲了,其實不是這個意思。
禪師的對話都很中肯,但是你為什麼不敢承擔呢?為什麼當別人在讚美你的時候,你不敢承擔呢?你不敢承擔,你的知見一定錯誤。當別人肯定你優秀,你應該接受別人的肯定,但是你還是要說你還要學習。我們現在的行者呢?現在的行者少了骨氣,也少了節氣。我們的心,要不卑不亢!不卑不亢,符合中道!不卑不亢,符合如實!我如實回答!為什麼這麼說呢?為什麼不可以看輕你自己呢?在《金剛經》裡面,當世尊講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世尊講完這段話後,須菩提就問世尊一個問題:「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也就是須菩提懷疑說,世尊現在當面為他開示,須菩提他能體證也能接受,但是須菩提懷疑未來世其他的眾生,他聽到這樣的教授,這樣的法義,他能如實相信嗎?一樣的道理,《傳心法要》上到今天,同學們有人真實相信這種道理嗎?當然有人。不然我現在跟誰講話?你們就是相信所以才坐在這裡嘛!我現在在跟你們講話,如果你們都不相信,那這個課就沒戲唱了。
你們會懷疑說,佛法的道理這麼高深,這麼難以想像,那真的有人能真實相信嗎?你們相信嗎?你們相信,但是真實嗎?不真實。你們相信,為什麼?因為是佛說的。但為什麼不真實?真實的狀態不是相信這種狀態,你們沒看到真實法,沒看到真理,所以你們現在是相信,但不真實。接著佛怎麼說呢?「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佛第一句話就跟須菩提講,你不要這麼說。你不要這麼說,為什麼?「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世尊說他滅度之後,後世如果有這麼一個人,他能持戒修福,是一個真實修行的人,那麼他聽到《金剛經》這段話,他能生起信心,而且是生起真實的信心。我們這班同學,你覺得你是這輩子才修行的嗎?你覺得你是遇到我之後才開始聽佛法的嗎?你誤會了,其實你已經修很久,但是你忘記了。所以世尊後面講這一段話:「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這段話就是告訴你說,你是曾經長久種諸善根的人,如果你不是那樣的人,你不會想學佛,你沒辦法持戒修福,你也不會修習《金剛經》那本經典。
但是難道只有《金剛經》這樣講嗎?《法華經》有沒有講過類似的話?你今天能夠上《法華經》的人,你沒有來歷嗎?你一定有來歷!沒有來歷的人不會長期上《法華經》。所以這段話就是告訴你,你不要看輕你自己,你不要一天到晚說「你業障重」。甚至有的人更糟糕,他常常這麼講:「我過去一定是造什麼孽?所以我今天才怎麼樣。」不要講這樣的話,因為這樣的話是連續劇在講的。沒有錯,你過去曾經造很多的孽,但是你過去也修很多的善,你過去也曾經是個很好的修行者,只是你現在腦袋有一些東西你還沒辦法回憶起來的,很多東西你忘記了。所以才跟你講說,你不要看輕你自己。但是相對的,你不要太膨脹,太高估你自己,認為你現在已經是成就者,不用再修了,這樣不但障礙你自己,也會被別人笑。所以一開始就跟你談「肯定自我」這個概念,雖然不要執著自己,但是要肯定自己,你沒有肯定自己,你不會成功,也不會成佛。這個概念很重要!
聽了這段對話,你以後跟別人應對,你可以這樣回答嗎?原則上前面那句話就是人家讚美你,你要不卑不亢的接受,但是你的回應呢?也很自然,你能很中肯如實的回答。
丈曰:「巍巍堂堂,當為何事?」師曰:「巍巍堂堂,不為別事。」便禮拜。我們內在每個人都有很強的自我意識,心中都很傲慢,但是當你靜靜看別人的對話,你會不會覺得,別人的程度早就高過你太多太多,你有沒有覺得,他們的對話是你答不出來的;也就是說,你不是那樣的人,你答不出來。所以有時候看公案,懂不懂先擺一邊,看到別人的對話,我們就當肅然起敬;就會覺得,唉呀!真的,這些人我們太讚歎了!怎麼能夠這樣的應對進退。他們是什麼樣的胸懷,什麼樣的智慧,他們為什麼能夠這樣對答呢?我們一輩子跟別人講話,絕大部分都講什麼話?都是講廢話,鬼話。這句話是百丈禪師繼續問:「這位志氣很高的修行者,你今天來這裡是為何事?」黃檗禪師回答:「巍巍堂堂,不為別事。」不為別事,有沒有事?有。什麼事?「只為一件事。」哪件事?「生死事大,明心見性,祖師西來意」。雖然世間上每個人想法不一樣,為的事情不一樣,但是你們學佛只為一件事,就是「生死事大」。這件事是共同的,沒有例外;如果你有例外,你不懂佛法。黃檗禪師講完之後便禮拜百丈禪師。
你們有時候很有禮貌,看到師父就一下給他拜下去,拜完起來你就跟師父講:「請師父開示。」你不問問題,一下子就請師父開示,師父要開示什麼呢?現在的法師比較好當,為什麼?因為你只是要開示,師父可以亂說,知道嗎?你只叫我開示,所以我講什麼,你都要聽,那我就叫你「在家要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姐妹,要多多幫助別人,不要常煩惱」,這樣開示也沒有錯啊!所以,現在的法師很好混,因為都讓信徒寵壞了,信徒不知道怎麼問問題,所以法師也不會進步。你沒有問真正的問題,只開口請別人開示,這是不負責任的想法。所以,要會問問題;當然有時候法師跟你講的,並不是你想要的答案,但是你自己要什麼答案,你也不知道。
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從上」,是多上?遠至過去諸佛,近至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傳法給大迦葉,一直傳到初祖菩提達摩,菩提達摩再傳到六祖惠能,代代相傳。簡單的說,「從上宗乘」就是禪宗的教義。黃檗禪師直接問的問題就是「禪宗這個宗門的教義是如何啊」?
丈良久。黃檗禪師問的問題,百丈禪師沒有馬上回答;只靜靜的坐在那裡,很久都沒有說話。不說話也是一種回答,回答不見得要說話。如果你問法師問題,問了之後,他靜靜的,一般人總會覺得,他應該是不懂,這叫做腦袋。我們的腦袋總是認為說「我問你,你答不出來,你靜靜的,你在想哦!所以你答不出來。」
有個同學問說:「師父,有時候你在講課,為什麼突然停頓?」我就問他說:「那你說為什麼呢?」他就說:「師父應該是在想怎麼回答?」我說:「好啦!有時候停頓,是真的在那邊想怎麼跟你回答。」但有時候我不配合你的動作,因你的腦袋不習慣停頓,你的腦袋就像流水,你習慣一直想一直想,如果我配合你的動作,你那個一直想不會改變,所以有時候我幫你踩一下,不配合你的動作,就是希望你能夠稍微停頓一下。就在這稍微停頓一下,看你看到什麼?
師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黃檗禪師說:「禪師,你不可以不回答,如果你不回答,那後面的人怎麼辦呢?後面的法怎麼傳呢?那這樣不就斷絕了嗎?」
丈曰:「將謂汝是個人。」乃起,入方丈。百丈禪師被他這樣一逼,這個「將」,我把它解讀兩個意思,一個是將來;一個是將軍,在這裡我比較喜歡把它作將軍解。為什麼喜歡作將軍解呢?因為他是個人才,「汝是個人」,是說「你是個人才!」沒講什麼話,百丈禪師就肯定他。你今天會這樣問答回話,就是不簡單的人物,不然你不會這樣。天下人如過江之鯽,要在江中等到一尾蛟龍實在太難了,但今天已經等到了,就應該好好跟他對話對話嘛!但是百丈禪師有這樣嗎?「沒有。」百丈禪師就站起來,走進他的方丈室,不理他。
師隨後入,曰:「某甲特來。」黃檗禪師追進方丈室,進去之後就講:「某甲特來」,這句話講得很肯定,他們講的話都很肯定哪!這是妄想嗎?這不是妄想,他們心心相印,確實是這樣。
丈曰:「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百丈禪師回答說:「如果你真是這樣,真的是我講的那個人才,那以後你就不要辜負老納,知道嗎?」原則上,我們說這個人是可造之才,其實我們講的就是這個人的素質跟態度,透過這樣的素質跟態度,我們就可以判斷你是不是可造之才。所以這裡講的不是這個人的學問跟知識,也不是這個人的能力跟聰明。所謂可造之才,原則上是看他潛藏的素質,這個素質最重要的就在「態度」兩個字,這是最重要的關鍵。開悟兩字或許很抽象,或許也很困難,但今天你的態度正不正確,我覺得並不抽象。一個人的態度有抽象嗎?不抽象。我所講的態度不是指你對別人,是你對你自己。你自己有沒有這種態度你知道,也就是說,你對你自己的態度不好,怯懦的眾生對自己的態度都是不好的。是悟道比較難呢?還是態度比較難?「悟道比較難。」態度只要你願意的話,是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改變的。絕大部分人都會緊張,因為對自己沒有信心,絕大部分的人都會畏懼,因為不夠勇敢。「信心」也好;「勇敢」也好,它雖然不是悟道,但那是一種內在的特質,你們一定要培養這種特質,這兩種特質一旦出現,你要悟道就很快。
我看過一些充滿信心跟勇氣的人,這樣的人做什麼都會成就,所以你首先要培養你是這樣的人。就像你今天真的是為生死事大,是為一佛乘來向我請法,我也覺得你是個人才。好,這樣你就不要辜負我。比如說朱銘去找楊英風,假設朱銘沒有表明他堅定的意願,你覺得楊英風會收他嗎?「不可能收他的。」我們就是因為沒有看重自己,所以我們也沒有看重別人;因為你沒有看重自己,所以你也沒有看重你自己學的東西,因為都沒有看重,所以很散漫。好好看看你自己的心,你有看重自己嗎?
百丈禪師跟黃檗禪師這一段,我再用另外一個角度來講,也就是說你是真正要學,而且你也真的是對得起你自己,所以你去參訪。你去參訪一個人,你內在一開始就瞧不起那個人,那你去參訪他有用嗎?一點用處都沒有。那沒有用你為什麼還要去呢?因為你也不知道你在做什麼,你就是攀緣,只是這樣而已。你喜歡到處逛逛,到處看看,但是你對誰都不服氣,結果你去不是要去參訪別人,你去只是要表達自己的意見,自己的看法,所以你去參訪別人,變成是要去講給別人聽。你看不起那個人,你不用勉強去參訪他,你可以去參訪你看得起的人,但問題是你看得起的人你又找不到,你找得到的你都看不起,那怎麼辦?你就以經典為師。你現在知道我在講什麼人嗎?我在講我自己啦!我自己就是這種臭脾氣。所以我就乖乖的,以經典為師,你自己知道自己,就好好的做自己,你不要到最後,什麼都不是。
丈一日問師:「甚麼處去來?」曰:「大雄山下采菌子來。」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即打丈一摑。丈吟吟而笑,便歸。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
丈一日問師:「甚麼處去來?」一直等到時機成熟的那一天,我為什麼會停頓呢?我為什麼會說「甚麼處,去來」?我把它分兩段,你有沒有注意?「甚麼處」是什麼意思?「心。」好,答得不錯。「去來」就是作用,所以你在「甚麼處」把它寫「體」;「去來」旁邊寫「用」,「體、用」。你在什麼地方來來去去?你在什麼地方喫飯睡覺?你在什麼地方語默動靜?你在什麼地方產生妙用?你如果答說心啦!自性啦!佛性啦!空啦!這都叫門外漢。直接說!在什麼處?「空。」你看,門外漢。現在問你,你都不要講名相給我聽,你講名相給我聽都是門外漢。人家內行人一聽都知道你是書呆子、佛呆子,意思就是你不了解,你才會這樣說。
你講的這個字對嗎?這個字一定對,不過你知道它的意思嗎?一定不知道。你講的每一句話都對,但是每一句話你都不知道它的意思。有時候我們為什麼公案看不懂?因為你都用佛法的概念看公案,你不是以一個消化的人去看公案。兩個高手過招,他們都是已經消化過的人,所以你不知道他們在講什麼。你以後看這個公案,不要一直用你那個概念去看,那些經典,那些名相他都消化了,他不會用那個名相來跟你回答,只要用名相來回答,就叫教條。
曰:「大雄山下采菌子來。」大雄,是出自《法華經》裡面「大雄世尊」,「大雄」是佛的意思。「大」就是偉大,「雄」就是英雄,「大雄」就是偉大的英雄。大雄山,他這裡有兩個意思,第一、大雄本身是佛的意思;第二、百丈山它又叫大雄山,或是叫大雄峰,也就是百丈山的別名剛好叫大雄山。所以這裡面就暗指兩個意思,一個指的是佛;一個指的是百丈禪師。百丈禪師問:「你什麼處去來啊!你在什麼地方產生妙用啊!」黃檗禪師回答:「我在大雄山」,大雄山就是自性,我在我自性當中產生妙用。怎麼妙用呢?「山下採菌子來」,菌子就是很微細的東西,也就是說在一座大山當中,任何微細的東西他都看得很清楚,意思就是他內在的起心動念,他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禪師都用他生活上的東西來回應,但因為大家都是內行人,所以百丈禪師聽到,他當然知道你在回答什麼。我現在問你,你的心就是大雄山,大雄山下的一草一木你都清清楚楚嗎?黃檗禪師用這種方式來形容他自己的心境,那巧妙的地方在哪裡?既然徒弟這麼高明,師父難道會不高明嗎?所以既然黃檗禪師做這樣的譬喻,百丈禪師直接就接他的話,怎麼接呢?
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黃檗禪師以一座山來形容自性,那山中最大的蟲是什麼?老虎。「大蟲」就是老虎。那如果有人問你說,你有見到老虎嗎?我們一般人會怎麼回答?「見」。但是黃檗禪師會這樣回答嗎?黃檗禪師作什麼動作?他就學老虎叫一聲「吼!」你不覺得這個畫面有多麼好玩嗎?這比你說「見。」這樣的回答生動得太多。那你說,這樣有沒有見?
你會覺得說,奇怪,為什麼這樣的人,會這樣回答,好奇怪啊!為什麼?因為他的腦袋跟我們的不太一樣。我們的腦袋是教條式,我問你從哪裡起作用?你說從心起作用;我問你說你現在有沒有見性?你說師父,我已經見性了。這種回答就是教條式。你在還見大蟲麼?旁邊寫幾個字,叫做「見性否?」;師便作虎聲,是回應「已見!」
前面是徒弟不放過師父,後面是師父不放過徒弟,前面你要苦苦追尋真理,但是當你已經要去問真理的時候,師父就要苦苦追問你,看你對真理是真懂還是不懂,就是這樣追來追去。那現在是你追我,還是我追你?現在我們誰都不追誰,你也沒有追我,我也沒有追你!為什麼?第一、不敢追;第二、還沒有追的時機。
丈拈斧作斫勢。師即打丈一摑。丈吟吟而笑,便歸。當黃檗已經作出虎聲,其實就是很清楚表示他是見性之人。前面黃檗禪師他學老虎叫,那既然你是老虎,所以百丈禪師就著手上拿個斧頭,就來砍老虎,那個「斫」就是砍。而既然你拿斧頭要砍老虎,有沒有?那當然虎掌就撲過來了,就打百丈禪師一個耳光。你覺得這一幕如果外面的人看到會怎麼說?「哪有這種徒弟?」如果有這種徒弟,他早被師兄弟圍堵,逐出師門,排斥掉了。「丈吟吟而笑,便歸。」你看,他的師父很高興。
這個公案,其實我自己在看,它不只是有趣而已,憑良心講,我在看這個公案並不是只有文字,我還可以看到畫面,就是那整個對話的畫面。這個公案這麼生動,這麼活潑,他今天所以會這樣問,會這樣做,就代表說,懂不懂已經不是用說的了,而是他就直接演出來給你看,他不要說的啦!而我們是說了老半天也仍然搞不清楚。所以,你們可以看得到,這種層次已經離開文字了,他不是抱著經典,在那邊解釋經典,而是整個過程你會知道說,哎呀!這一對師徒啊!都是高人,真是高人!現在的人要見到這一幕發生,幾乎是難上加難,師徒之間能這樣印證的太少。
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你看,講得多幽默。他這樣的開示有沒有人聽得懂?沒有。所以他講這句話是講給誰聽?講給黃檗一個人聽啦!誰聽得懂他到底在講什麼呢?這就像我們在上課,有時候我們突然講某些話,有的人在網路上聽我們的課,他聽到我在講某些的話,有時候他不知道我到底在講什麼?因為只有當天在現場的當事者才知道。所以黃檗禪師他開悟了!開悟之後當然就成為一方的大德。
師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唐宣宗為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師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為?」師便掌。彌曰:「太粗生!」師曰:「這裡是甚麼所在!說粗說細。」隨後又掌。宣宗繼位,賜封黃檗作「粗行禪師」。裴休在朝,奏改為「斷際禪師」。
師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唐宣宗為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鹽官」是一個鎮,在浙江省,黃檗禪師本身是福建人,黃檗禪師因為到處參訪,最後回歸江西,但他現在是在浙江的一個佛寺。那天,他在殿上禮佛,當他在禮佛的時候,這時剛好旁邊有一位沙彌,這位沙彌後來當皇帝,叫唐宣宗;就像朱洪武一樣,朱洪武小時候也當過沙彌,所以我們就稱他為沙彌皇帝。既然是沙彌皇帝,就代表說這個沙彌本身程度也很好。那天那位沙彌看到黃檗禪師在那邊禮佛,等黃檗禪師禮完佛之後,他就問黃檗禪師說:「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沙彌的意思是說,佛法不離佛、法、僧三寶,但是都應該無所求,那既然都無所求,長老,指的就是對黃檗禪師的尊稱,那你剛才拜佛是在求什麼呢?你看,真是關老爺面前耍大刀。
師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常的意思就是說,平常該做什麼就做什麼,該拜佛的時候就拜佛,該掃地的時候就掃地,該吃飯睡覺就吃飯睡覺,所以這個「常」,就是說平常心就應該是這個樣子。但如果要講它更深的內涵,你在旁邊寫八個字,「無心而為,無求而作。」這八個字懂了,《傳心法要》你就看懂了,《傳心法要》是在說這個而已。無心,無求,無為,就是這樣拜而已。
彌曰:「用禮何為?」師便掌。所以好在你沒去找黃檗禪師做師父,要不你早就被打死了。黃檗禪師已經跟他回答說,只是這樣拜而已,沒有為什麼!那個不長眼的沙彌又說:「那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呢?」這就像說我在拜佛,然後你跑過來問說:「師父,你為什麼要拜佛?」我就給你打回去,知道嗎?就是這個樣子。佛法本來很單純,我們就是想太多,一件很平常的事,在你眼中看起來好像什麼都很奇怪,佛法越學你越奇怪,每個動作你看到了,好像都有什麼特別意思似的。
彌曰:「太粗生!」沙彌就說:「哦!這位禪師太粗魯了!」你是個修行者,怎麼可以打人呢?尤其你是長老,我是沙彌,怎麼可以以大欺小呢?
師曰:「這裡是甚麼所在!說粗說細。」隨後又掌。又給他打下去。所謂「這裡是什麼地方?」你不要單純解釋成說這裡是大雄寶殿,是莊嚴的佛殿,你在旁邊寫幾個字「於無分別處」,講的就是自性,自性本來沒有分別對待;你在「說粗說細」旁邊寫三個字「說分別」。於無分別處說分別,真的是該打該揍。
如果按照黃檗禪師的教化方式,你們以後敢來找我嗎?我常說:「說的有用嗎?」你不要以為說理有用,有的東西不說才有用,像這個,用打的才更有用。問題是,打你,我就要上法院,所以我也不敢。那小沙彌現在還小,但總是會長大的,隨著時間一天天過去,有一天,小沙彌當皇帝了。
宣宗繼位,賜封黃檗作「粗行禪師」。你看,這個沙彌小時候的印象到現在還記得,除非不當皇帝,如果做皇帝我就封你為「粗行」,「粗行禪師」就是粗魯的禪師。
裴休在朝,奏改為「斷際禪師」。還好!有裴休宰相,因為裴休是黃檗禪師的弟子,所以裴休當然上奏,講一段好話勸皇帝,那個奏摺內容就是說:「哎呀!皇上!你誤會黃檗禪師了,其實他當初打你,是因為什麼樣的因緣,他有什麼樣的啟示。」誤會終於澄清了,所以宣宗改封他為斷際禪師。
相國裴休(七九一至八六四),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也。公入寺燒香,主事祇接。因觀壁畫,乃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僧真儀。」公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僧皆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曰:「可請來詢問得否﹖」於是遽尋運師,公之欣然曰:「休適有一問,今請上人代酬一語。」師曰:「請相公垂問。」公即舉前問,師朗聲曰:「裴休!」公應諾。師曰:「在什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曰:「吾師真善知識也。」
相國裴休(七九一至八六四),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也。《傳心法要》的整理人就是裴休,所以最後就要講到他。「相國裴休出生於西元七百九十一年,卒於西元八百六十四年,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也。」裴休宰相出生在河東聞喜,聞喜在今天山西省,是山西省河東人。
公入寺燒香,主事祇接。裴休宰相有一天他到一間寺院燒香禮佛。「主事祇接」,這個主事不一定是住持,有可能是知客,依裴休的身份,因為他是宰相嘛!知客一定會通報,所以應該是住持親自接待,「祇接」就是接待的意思,由住持來接待。
因觀壁畫,乃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僧真儀。」裴休禮完佛之後看到一面墻壁,那個墻壁上掛有一幅圖畫,所以裴休就隨口問說,這是誰的畫像呢?如果墻壁上掛的是人物的像,他一定會問說:「這個是什麼人的畫像呢?」住持就回答說:「這是一位高僧的肖像。」「真儀」就是肖像,「真」就是肖像的意思,我們常問說:「你去哪裡?」「我去寫真!」寫真就是畫畫。也就是住持回答說:「這個是高僧的肖像。」
公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僧皆無對。重點就在後面這句,這句實在是問得太好了,這個裴休就問說,這個畫像是在這裡,但是那高僧現在在哪裡呢?你會這樣問嗎?你不會。我們去寺院看那個羅漢相,看那個釋迦牟尼佛八相成道,看很多的相,但你會問嗎?你們不要學了這個公案之後,每次去到寺院你就處考人家。「僧皆無對」,沒有人答得出來。
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裴休知不知道他們答不出來?知道。所以裴休就給他們一個下台階,黃檗禪師到別人的寺院去掛單,人家根本不知道他的身份,但大家相處一段時間之後,覺得說,這個人好像跟別人不一樣。所以裴休就問說,寺裡有沒有懂禪的人呢?那個住持就講說,唉呀!最近有一位出家人來這邊掛單,在寺院裡面做一些執事,我平常觀察他,他好像是個禪者。
公曰:「可請來詢問得否﹖」於是遽尋運師,裴休就說,那是不是可以請他來以便我能請教他一下,那個住持就急忙去尋找。「運」是希運,「運師」就是黃檗希運禪師,住持就急忙趕快去找黃檗禪師來。
公覩之欣然曰:「休適有一問,今請上人代酬一語。」師曰:「請相公垂問。」黃檗禪師來的時候呢,這個裴休宰相看到他,就很欣悅的對他說:「我剛才問寺方一個問題,但因為大家都答不出來,所以是不是能請上人代為回答?」上人是尊稱。黃檗禪師就說:「那請相國您賜問」。
公即舉前問,師朗聲曰:「裴休!」公應諾。重點來了,這個裴休他現在把剛才問的問題重新講一遍,他講什麼問題你還記得嗎?「真儀可觀,高僧何在?」講完之後,黃檗禪師就大喊一聲:「裴休!」公應諾。你找到人了嗎?你知道高僧在哪裡了嗎?回答的那個人是誰?高僧!所以高僧的生命在哪裡?我的生命在哪裡?我的生命就是現在我在講話這裡!裴休應「諾。」這個能回應的心,就是高僧的所在,就是生命的所在。每個人都有不生不滅的生命啊!
師曰:「在什麼處﹖」裴休已經答諾了,黃檗禪師再逼他:「在什麼處?」
公當下知旨,「當下」,也就是當他答「諾」的時候,黃檗禪師馬上逼問他:「在什麼地方啊?」這一逼問,就在這一逼問之下,裴休就開悟了,就是逼他去找到自己了。
如獲髻珠,曰:「吾師真善知識也。」這個髻珠也是出自《法華經》,國王頭上就只有一顆髻珠,這顆髻珠不輕易送給別人。這裡就是譬喻裴休獲得最上乘法了,所以裴休讚嘆說:「唉呀!黃檗禪師,您真是我的大恩師,大善知識啊!」
這些公案,你好好回去品味,不要把它當成公案看,你把它當成你日常生活當中就是公案,其實你日常也常常做這些動作你沒察覺,你沒察覺這個就是啦!就是這個啦!這樣知道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