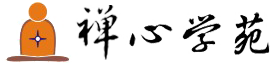印順導師的一生
二四 有緣的善女人
來臺灣定居,有緣的人不少。有緣,不只是欣喜,而也會苦惱的。佛法說:「愛生則苦生」;為了愛護,或過分的熱心,……也會引到相反的方向。因緣,原來就是有相對性的。善男子當然也不少,而所以要寫幾位有緣的善女人,那因為留下些值得回憶的因緣。
一、慧泰:在我來臺灣不久,住在善導寺。一天傍晚,我忽然走向大殿,看看流通處(大殿西南角)。一位五十來歲的太太,衣著樸素,行動緩慢的進寺來。禮了佛,問旁人:香港來的法師,是在這裏嗎?有人就為他介紹,向我頂禮。看看時間不早,說:「我明天可以來請開示嗎」?我說:「可以」。他就緩慢的 [P141] 走了。他的面容憔悴,神情憂鬱而極不安寧。我想:世間真是多苦的世間。
他再來時,說自己姓曾,過去是辦教育的。為了學校,曾請政府依法懲處不法者。但他的愛女,忽然卒病死了。這是他的罪惡,害死了他的愛女。為了愛念女兒,就悔恨自己的罪惡,在愛而又悔的苦惱中,不能自拔,問我有沒有救度的方法。我為他略示佛法的因果正理:為維護教育而依法懲處,即使執法者過嚴,也不能說是你的重大罪惡。死亡的原因很多,但依佛說,決沒有因父母而使兒女病死的道理。夫妻也好,父母與兒女也好,都是依因緣而聚散的。如因緣盡了,即使沒有死,也可能成為仇人或路人一樣。經過幾次開示,神情逐漸開朗而安寧起來。後來歸依了我,法名慧泰。我從不問信徒的家庭狀況,到第二年(四十二年)初夏,才知道慧泰是立委曾華英。
慧泰的個性很強。慧泰對我,對精舍,特別是對仁俊,可說愛護備至。但也許護法的過於熱心,也不免引起些困擾。好幾年前,幼兒有病,使他非常的困惱。廣欽和尚勸他逃,慧泰問我,我說:「有債當還,逃是逃不了的」!他終於堅 [P142] 忍的支持下來。
二、慧教:這是一位青年就學佛的,勤勞儉樸,多少能為信眾們介紹佛法的善女人。他原是月眉山派下,法名普良,沿俗例也有徒眾。他大概是在基隆歸依我的,法名慧教。後來移住到臺北,往來也就多了。他有領導信眾,主持道場的熱心,所以讀了我的『建設在家佛教的方針』,覺得非常好。在慧日講堂的籌備中,他非常熱心,與慧泰也談得來。他以為:福嚴精舍是為法師們建的,慧日講堂是為在家弟子建的。這與成立講堂的意趣,不完全相合,所以熱心聽法,而多少要不免失望了!
三、宏德:五十二年(五十八歲)秋天,蘇慧中居士(也是一位難得的善女人)陪他來聽經,首先有一條件,只聽經,不歸依。我對慧中說:「講經是為了大家聽法,好好聽就得了」。每次來聽,都有兒女相陪。來了就聽,聽了就去,我也沒有與他談話。到了講經圓滿,他才進來坐一下,並問有關靜坐的問題。後來據慧中說:他家是開毛紡廠的,先生意外的去世了。有事業,兒女還小而丈夫 [P143] 就去世,這是難免會憂苦增多的!
五十三年(五十九歲)元旦,他去新竹參加福嚴學舍的畢業禮,請求歸依,法名為宏德。那年秋天,來嘉義妙雲蘭若。談起有人勸他共建道場,我說:「如奉獻三寶,就要多些人來共同發起。如將來自己也想去住,那就以人少為妙」。不久,他胰腸炎復發,危急到準備後事了。他說:「那時自知無望,也就沒有憂怖,一心繫念三寶。忽而心地清涼寧靜,人就迷迷糊糊的睡著了。等到醒來,病情迅速消失,連醫生都感到意外」。於是他感到三寶的恩德,人生的無常,急急的建成了報恩小築。大殿不大而莊嚴,是他與女兒們設計的。報恩小築的建設,為了報答親恩,也為自己的長齋學佛著想。五十四年(六十歲)春落成;第二年我也住到報恩小築,他(住在家裏)時常來禮佛。到五十八年(六十四歲)秋天,我回到妙雲蘭若,已住了三年多了!
宏德對我的四事供養,過於優厚,使我有點不習慣,但說他也沒有用。他為我出版了『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我要去星、馬,他就自動的 [P144] 備辦了小佛像、念珠等,讓我拿去結緣。他的承事供養,勝過了對父母的孝思。他的婆婆、姑母、二姑、二女兒,連初生的長孫,也結緣歸依,全家都叫師父。我要離開小築,一再勸他請法師供養,他固執的不願意。以不歸依為條件而來,而又自動的歸依了,這只能說是有緣了。
宏德為了事業(先生去世,他就沒有去顧問),為了兒女,經常有些困擾。也許與性格有關,堅強中略有些忽遽的神情。現在兒女都漸漸長大了,個個聰明能幹。我想,不要幾年,如兒女全都長成而獨立,他應該能更安祥地奉佛了!
二五 學友星散
人生的聚散無常,真如石火電光那樣的一瞥!
與我共住較久的,現在是:演培在星洲福慧講堂;妙欽與續明死了;仁俊在美國弘法;妙峰在紐約成立中華佛教會;印海在洛杉磯成立法印寺;幻生也遊化美國;常覺也離開了福嚴精舍。其他是演培與續明領導的學生,雖在精舍住過, [P145] 我多少有隔代的感覺。我缺少祖師精神,沒有組織才能,所以我並不以團結更多人在身邊為光榮,而只覺得:與我共住過一個時期的,如出去而能有所立──自修,弘法,興福,那就好了!
我與演培、妙欽,在二十九年底就相見了。演培蘇北高郵人,可說是與我共住最久的一人!從四十二年到四十六年夏天,對福嚴精舍與善導寺,我因病因事而不在時,由他代為維持法務,可說是幫助我最多的一人!我一向以平凡的標準來看人,演培是有優點可取的。他熱心,為了印『印度之佛教』,他奉獻了僅有的積蓄。預約、出售『大乘佛教思想論』的餘款,樂助為福嚴精舍的增建費。他節儉,但並不吝嗇於為法,或幫助別人。他的口才好,聲音也好,所以到國外去宣講佛法,到處有緣。於佛法也有過較深的了解,如能一心教學,教學相長,偶爾的外出弘化,那是最理想不過的了。他多少有蘇北佛教的傳統,與我一樣的缺乏處眾處事的才能(缺點不完全相同)。他的處眾處事,如遇了順緣,就不能警覺,往往為自己種下了苦因。他有點好勝、好名,「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如 [P146] 為名而珍惜自己,不正是善緣嗎?他自從辭退了善導寺,似乎非要有所作為不可。住持日月潭玄奘寺,也許就是出於這樣的一念吧!人是不會沒有缺點的,希望能在不斷的經驗中,能從佛法的觀點,容忍的、警覺的去適應一切,創造一切!
對我一生幫助最大的,是妙欽。我與妙欽在四川共住的時間,不過兩年多,所以,以其說由於共住,不如說由於思想傾向的相近。他曾編『中國佛教史略』(後由我改編),『初機佛學讀本』。他對佛學,有條理,有思想。文字、講演、辦事,都很好。西湖佛教圖書館,就是我們的共同理想,也可說是促成他去菲的一項因素。三十八年就去了菲律賓(又去錫蘭深造多年)。大陸變色,他將為佛法的熱誠,寄望於菲律賓的佛教,希望能從性願老法師的倡導中,有一新的更合理的發展。但性老有為法的熱心,觀念卻是傳統的;我雖去菲律賓,也不能有所幫助。為時代與環境所局限,心情不免沈悶。四十九(?)年起,負起了主導佛教創辦的能仁學校的責任。時代與環境的局限,是不能盡如人意的。唯有本著能進多少就是多少的信念,才能不問收穫而耕耘下去。他的「心情不免沈悶」, [P147] 使他在六十五年,因患肝病而去世了。他是我所不能忘懷的一人!
續明,河北人。共住漢院的時間並不長。從雪竇寺編輯『太虛大師全書』起,才一直在一起。四十二年春,續明來臺灣編輯『海潮音』。四十五年秋,我要住結核病院,有切除肋骨的打算,這才與他(正在靈隱寺掩關)商量,要他移到精舍來掩關。四十七年冬,我從菲回來,又以時常要出去為理由,請他接任精舍的住持,一共維持了五年。從雪竇到臺灣,他始終給我很多的幫助。續明是外貌溫和而內性謹肅的。對自己的弟子與學生,特別關切,真是慈母那樣的關護。對沙彌與女眾的教導,沒有比他更適宜的了。他曾親近慈舟老法師,所以掩關以來,有了重戒的傾向。他主辦靈隱佛學院,首先調查靈隱寺受具足戒者的人數,他是想舉行結界誦戒的。寺方懷疑了,幾乎一開始就辦不下去。其實,何必顧問寺眾呢!五十年初,主辦福嚴學舍,建議全體持午。這不但有舊住者散去的可能,而且慧日講堂沒有持午,講堂與精舍,不將隔了一層嗎?他嫌我不支持他。這些不能說是缺點,只是從小出家於寺院(以小單位為主),不能關顧到另一方面而 [P148] 已。續明的身體,看來是很實在的,然在香港就有腦(?)病。全力關護於學院學生,病也就越來越重了。五十三年,辭卸了精舍的住持,作出國的遊化活動,卻想不到竟在印度去世了!他正在香港、越南、星、馬遊化,又以出席佛教會議而死在佛國。如死後哀榮也是福報的話,那與我有關的學友,連我自己在內,怕沒有比他更有福了!
仁俊,是在香港淨業林共住了一年多的。在與我共住的人中,仁俊最為尊嚴,悟一最為能幹!仁俊的志趣高勝,所以不能安於現實。過分重視自己(的學德),所以以當前自己的需要為對的,絕對對的,需要(即使是自己過去所同意的,所反對的)就可以不顧一切。
仁俊是四十四年初到精舍來住的。我四月上旬從菲回來,他早有過住中壢圓光寺的打算了。四十五年秋,我將住結核病院,請他為大家講一點課,他不願意,聽說碧山岩要請法師,就自動的去了(碧山岩如學,曾說我不愛護徒孫,不肯派法師去。不知道這是要自己需要才有可能的)。起初有十年計劃,後修正為五 [P149] 年。據說:讀了戒律,知道比丘住比丘尼寺是不合法的,感到內心不安。要碧山岩為他另行(離遠一些)建築,否則住不下去。四十七年底,他來參加靈隱佛學院的開學禮,大家知道他住不安了,也就勸他回隱院講課,他就這樣離開了碧山岩(住了二年多)。隱院(續明主持)還是住不安,四十八年秋季開學期近了,課程早排定了,他卻一走了事。先到碧山岩,要求住過去住過的地方。不成,就由高雄的道宣介紹,住屏東有規模的尼眾道場──東山寺(不肯為眾說法結緣)。可能是五十年秋季(?),仁俊回到了精舍(大概是續明約他回來的)。年底,演培、續明、仁俊,自己商量定了,再由我與大眾,在精舍舉行了一次會議,議決:五十三年春,精舍由仁俊主持,講堂由演培主持。這是仁俊自動發心,而又當眾承認通過的。我雖然感到意外,但也當然是歡喜了。這一次的決議,仁俊與演培,都不曾能履行諾言。五十三年,仁俊自己建立同淨蘭若。五十七(?)年,仁俊又有去德山岩(尼寺)掩關的準備;終於在六十一年,到美國遊化去了。非建不可的同淨蘭若,應該又有不安之感吧!這當然不是為了經濟,而應該是 [P150] 不能「同淨」。仁俊的志性堅強,情欲與向上心的內在搏鬥,是怎樣的猛烈、艱苦!在這末法時代,是很難得的!然在他的性格中,沒有「柔和」,不會「從容」,只有一味的強制、專斷,而不知因勢利導。「柔和」與「從容」,對仁俊來說,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了!
仁俊與演培,為什麼都不曾能履行諾言?五十一年底,信敬仁俊而與我有緣的曾慧泰,為仁俊購置了土地。精舍的法師而值得人信敬供養,我是只有歡喜的。不過我立刻告訴慧泰:仁俊法師自動發心要主持精舍,並經會議決定,不要因此而起變化。五十二年(國曆)七月,仁俊來信,說要興建靜室。我請他履行諾言,對精舍,你要這麼辦就這麼辦。自行化他,在精舍還不是一樣。但是,非自建不可。起初,曾慧泰還說(仁俊說):「不會在未得導師允許前興建蘭若」,而到底在慧泰等護持下興建了。就這樣,自己發心,而又為自己的需要而取消。演培為什麼不履行諾言?他給續明的信上說:「講堂,我應回來為導師分擔一分責任的。但臺北的大環境,我實在不能適應。況且曾居士最不願意我負講堂之責 [P151] 的。……想來想去,以延期回臺為是」。這應該是我一生中最不可思議的因緣!護法們對學團內的學友,有緣或者沒有緣,原是免不了的。由此而引起學團的從分化到分散,總不免感到意外!
二六 寫作的回憶
我的寫作,有是自己寫的,有是聽講者記錄的,還有我只是列舉文證,說明大意而由人整理出來的。既然說是我的作品,當然要自負文責。如我有所批評,對方當然也會批駁我,我以為:「受到讚歎,是對自己的同情與鼓勵;受到批評,是對自己的有力鞭策:一順一逆的增上緣,會激發自己的精進」(『法海微波序』)。所以,我受到批評,除善意商討外,是不大反駁的。如澹思的『讀「談入世與佛學」後』,黃艮庸的『評印順著「評熊十力新唯識論」』等,我都沒有反駁,所以在寫作中,糾纏不已的論諍,可說是沒有的,我只是「願意多多理解(佛法)教理,對佛教思想起一點澄清作用」(『遊心法海六十年』)。這裡所錄出的,是 [P152] 篇幅較長或有特殊意義的。
二十年(二十六歲):到廈門閩院求學。上學期,寫了『抉擇三時教』,『共不共之研究』(虛大師曾有評論)。下學期,到了福州鼓山湧泉寺,寫有『評破守培上人「讀唯識新舊不同論之意見」』。這一年,可說是我寫作的開始。
二十三年(二十九歲):上學期到武院,為了探閱三論宗的章疏,也就寫了『三論宗傳承考』,『清辨與護法』。
二十七年(三十三歲):下學期,到了四川縉雲山漢藏教理院。年來,周繼武一再發表論文,以為『起信論』與唯識學相同,賢首法藏誤解『起信論』,乃成諍論。虛大師囑為評論,所以寫了『周繼武居士「起信論正謬」』。
二十八年(三十四歲):秋天,虛大師從昆明寄來林語堂的『吾國與吾民』,要我對有關不利佛教部分,加以評正,我受命寫了『吾國吾民與佛教』。── 出家來近十年了,部分的寫作,都沒有保存;還有些不成熟的作品,有些連自己也忘了( 署名「啞言」的『三論宗傳承考』,可以保留) ! [P153]
二十九年(三十五歲):住貴陽的大覺精舍,寫成『唯識學探源』一書,進入了認真的較有體系的寫作。
三十年(三十六歲):上學期,回住漢院。江津的支那內學院,發表『精刻大藏經緣起』;虛大師要我評論,我寫了『評「精刻大藏經緣起」』。這一學期,以力嚴筆名,發表『佛在人間』,『法海探珍』等,突顯了我對佛法的觀點。又為演培、妙欽、文慧講『攝大乘論』,筆記稿就是『攝大乘論講記』。
三十一年(三十七歲):住合江縣的法王學院。那年,寫了『印度之佛教』,『青年佛教與佛教青年』。上學期,為學生講『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演培筆記,成『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記』。下學期起,為演培等講『中論』頌,到下一年才講了,由演培筆記,成『中觀論頌講記』。
三十二年(三十八歲):在法王學院。去年十月,虛大師見到『印度之佛教』第一章「印度佛教流變之概觀」,撰『議印度之佛教』;我寫了『敬答「議印度之佛教」』。大師在這一年八月,又寫了『再議印度之佛教』,我寫了一篇『 [P154] 無諍之辯』(文已佚),寄給漢院虛大師,表示只是表示個人的見解,不敢再勞累大師。
與漢院續明等通函討論大乘,後改編為『大乘是佛說論』。
三十三年(三十九歲):上學期在法王學院。漢院妙欽寫了『中國佛教史略』寄來,我加以補充整編,作為我們二人的合編。唯識學者王恩洋,發表『讀印度佛教書感』。他對我的『印度之佛教』,相當同情,但對「空」,「有」的見解,大有出入,所以寫『空有之間』作答。
夏末秋初,回漢院。為同學講『阿含講要』,光宗等筆記,此即『佛法概論』一部分的前身。又為妙欽、續明等講『性空學探源』,妙欽記。
三十五年(四十一歲):在武院。法舫法師作『送錫蘭上座部傳教團赴中國』,以為印度教融化佛教成大乘;上座部才是佛教嫡傳。我不同意這一看法,所以寫了『與巴利文系的學者論大乘』。
三十六年(四十二歲):正月,在武院,寫了『僧裝改革評議』。初夏,到 [P155] 奉化雪竇寺,與續明、楊星森等,編纂『太虛大師全書』。編纂期間,為續明等講『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講記) ,又講『中觀今論』,都由續明筆記。
三十七年(四十三歲):春,在雪竇寺,繼續完成『太虛大師全書』的編纂。我寫了『佛教之興起與東方印度』及『評熊十力的新唯識論』。
三十八年(四十四歲):上學期,在廈門南普陀寺,成立大覺講社。將『阿含講要』補充改編為『佛法概論』,為講社同學講說。
夏末,到香港。住大嶼山寶蓮寺;中秋後,移住香港灣仔佛教聯合會;十月初,移住新界粉嶺的覺林,開始『太虛大師年譜』的編寫。
三十九年(四十五歲):『太虛大師年譜』完成後,三月移住新界大埔墟的梅修精舍。為演培、續明等講『大乘起信論』,演培、續明筆記為『大乘起信論講記』。自己寫了『佛滅紀年抉擇談』。
四十年(四十六歲):移住新界九咪半的淨業林。為住眾講『勝鬘經』,成『勝鬘經講記』,又講『淨土新論』,都是演培與續明筆記的。自己想寫一部『 [P156] 西北印度之論典與論師』,並開始著筆,斷斷續續的寫了一些。
四十一年(四十七歲):住淨業林。為住眾講「人間佛教」──『人間佛教緒言』,『從依機設教來說明人間佛教』,『人性』,『人間佛教要略』。這四篇,由仁俊筆記,但在預計中,這是沒有講圓滿的。了參在錫蘭,譯南傳的『法句』,我為他寫了『法句經序』。
秋天,到了台灣,住台北善導寺。寫了『華譯聖典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我到了台灣,環境有些變化,多數是為信眾講的,有些講稿也沒有整理的必要。長篇的寫作等於停止了,寫的與講的,大都發表在『海潮音』。
四十二年( 四十八歲):十一月,主持善導寺佛七,每日開示,常覺記為『念佛淺說』。
這一年,我寫了『中國佛教前途與當前要務』,『學佛三要』,『佛法與人類和平』,『信心及其修學』,『自利與利他』,『中國的宗教興衰與儒家』,『慈悲為佛法宗本』,『建設在家佛教的方針』,『佛書編目議』等。 [P157]
四十三年( 四十九歲):年初,在善導寺講而追記為文的,有『我之宗教觀』( 原題為『佛法之宗教觀』) ,『生生不已之流』,『一般道德與佛化道德』,『解脫者之境界』。秋天,在善導寺講『藥師經』,由常覺、妙峰筆記,成『藥師經講記』。
這一年,寫了『以佛法研究佛法』,『點頭頑石話生公』,『佛法有無「共同佛心」與「絕對精神」』?『我對慈航法師的哀思』,『大乘經所見的中國』,『我怎樣選擇了佛教』,『大乘三系的商榷』等。『大乘三系的商榷』,是應默如學長的商討而寫的,年底又寫了一篇『讀「大乘三系概觀」以後』。
四十四年(五十歲):去年底到菲律賓,新年在岷尼拉大乘信願寺說法,『佛教對財富的主張』(後改題『佛教的財富觀』,賢範、小娟合記)等。二月抵宿務,假華僑中學說法,有明道記的『切莫誤解佛教』等。四月初,由菲返台北,講『菲律賓佛教漫談』,常覺、妙峰記。
在新竹福嚴精舍,為學眾講『學佛之根本意趣』,印海記。『慧學概說』, [P158] 『菩提心的修學次第』,常覺記。歲末,因病在台北靜養,與常覺等閒談,常覺記為 『福嚴閒話』。
這一年寫作不多,僅有『欲之研究』,『佛缽考』等。
四十五年(五十一歲):寫了『從一切世間樂見比丘說到真常論』,『龍樹龍宮取經考』;『印度佛教與中國佛教之關係』,是應『中國佛教史論集』徵文而寫的。
四十六年(五十二歲):六月,講『泰國佛教見聞』於善導寺,常覺記。
這年的寫作,有『美麗而險惡的歧途』,『太虛大師菩薩心行的認識』,『教法與證法的信仰』,『北印度之教難』,『舍利子釋疑』。並應星洲彌陀學校的請求,為編寫『佛學教科書』十二冊。下學期為福嚴精舍同學講『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作『楞伽經編集時地考』。
四十七年(五十三歲):冬,應善導寺住持演培法師請,在善導寺講:『心為一切法的主導者』,『佛教之涅槃觀』,『修身之道』,都由慧瑩筆記。 [P159] 這一年,寫了『宋譯楞伽與達摩禪』,『論佛學的修學』。
四十八年(五十四歲):去年年底,到王田善光寺度舊年,才完成了『成佛之道』。這部書,起初(四十三年)在善導寺共修會,編頌宣講;四十六年下學期,又增補完成,作為新竹女眾佛學院講本,又為偈頌寫下簡要的長行解說:到這一年的年初才脫稿。
十二月,寫『發揚佛法以鼓鑄世界性之新文化』。
四十九年(五十五歲):為鄧翔海居士等講『楞伽經』。講此經已三次,因緣不具足,沒有成書,僅留有『楞伽經』的科判──五門、二十章、五十一節。
五十年(五十六歲):作『玄奘大師年代之論定』。
五十一年(五十七歲):夏,講『大寶積經』「普明菩薩會」於台北慧日講堂,後追記而寫成『寶積經講記』。九月底,在慧日講堂啟建藥師法會,每日開示,能度記為『東方淨土發微』。
這一年,寫有『論真諦三藏所傳的阿摩羅識』。 [P160]
五十二年(五十八歲):七月,盂蘭盆法會期間,講『地藏菩薩之聖德及其法門』,能度記。冬季,講天親菩薩所造『往生淨土論』(本名『無量壽經優波提舍願生偈』),後由顧法嚴記,名『往生淨土論講記』。
本年青年節前後,台北和平東路某教會信徒,夜訪於慧日講堂,並贈『新舊約全書』,希望我研究研究。我與『新舊約』別來已三十餘年,所以回憶而寫出『上帝愛世人』,『上帝與耶和華之間』。因香港吳恩溥牧師的批評,又寫了『上帝愛世人的再討論』。
五十三年(五十九歲):三月,於慧日講堂講彌勒菩薩造的『辨法法性論』,後由黃宏觀記錄,成『辨法法性論講記』。
四月初八日,在嘉義妙雲蘭若掩關,恢復內修生活。閱覽日譯的『南傳大藏經』;然後對『西北印度之論典與論師』的部分寫作,擴充為『說一切有部為主 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進行改寫。
這一年的寫作,有『漢明帝與四十二章經』;關中寫的『論提婆達多之破僧 [P161] 』,『阿難過在何處』?『佛陀的最後教誡』。
五十四年(六十歲):掩關期間,寫有『王舍城結集的研究』,『論毘舍離城七百結集』。教內人士,有提倡改穿南傳佛教式的一色黃,所以寫了『僧衣染色的論究』。
四月初八日出關。夏天,在台北慧日講堂,講『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偈頌,後由楊梓茗記錄為『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偈頌講記』。
五十五年(六十一歲):住報恩小築。夏天,寫了『法是什麼』。
五十六年(六十二歲):住報恩小築。那年是虛大師上生二十周年,作『略論虛大師的菩薩心行』。讀澹思的『太虛大師在現代中國佛教史上之地位及其價值』,深有所感,所以寫了『談人世與佛學』,以「大乘精神──出世與入世」,「佛教思想──佛學與學佛」作線索,表達些自己的意見。
秋天,長達四十五萬字的『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脫稿。在理想中,這是分別重寫『印度之佛教』的一部分。澹思──張曼濤評論為:「在 [P162] 現代文獻學的方法上,本書或不免還有些缺陷。 ‧‧但在爬梳與理清舊有的漢譯文獻來說,可斷言:已超過了國際上某些阿毘達磨學者」。
五十七年(六十三歲):住報恩小築。寫了『學以致用與學無止境』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年底,抵星洲,住般若講堂。
五十八年(六十四歲):在星期間,曾講『佛法是救世之仁』,慧理記(後與香港所講,慧輪所記的,綜合為一)。寫『人心與道心別說』。
夏初返台灣。香港韋兼善教授,將『成唯識論』譯為英文,我欽佩韋教授為學的精誠,寫了一篇『英譯成唯識論序』。中秋前,我重回嘉義妙雲蘭若。年底,費時兩年的『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五十六萬字)脫稿。
五十九年(六十五歲):這一年,寫成了『中國禪宗史』──『從印度禪到 [P163] 中華禪』。『精校燉煌本壇經』,是附帶寫出的一部。這部書的寫出因緣,是意外的。去年,中央日報中副欄,曾有『壇經』是否六祖所說的討論,引起論諍的熱潮,參加的入不少。我沒有參加討論,但覺得這是個大問題,值得研究一下。我覺得,問題的解決,不能將問題孤立起來,要將有關神會的作品與『壇經』燉煌本,從歷史發展中去認識。這才參閱早期禪史,寫了這一部;得到道安、聖嚴法師的評介。
六十年(六十六歲):春,寫了『神會與壇經』,這是批評胡適以『壇經』為神會及其弟子所作而寫的。夏天,深感身體的不適,所以寫了自傳式的『平凡的一生』,略述一生出家、修學、弘法的因緣;似乎因緣已到了盡頭。不久,也就大病了。
六十二年(六十八歲):十月,移住台中市校對『妙雲集』的靜室,隱居養病。那時,因『中國禪宗史』,得日本大正大學授予博士學位,引起『海潮音』的一再評訐,所以辭去『海潮音』社長名義,並發表『我為取得日本學位而要說 [P164] 的幾句話』一文。
六十四年(七十歲):初夏,『中國古代民族神話與文化之研究』脫稿。這是意外的一部寫作。在台中靜養時,偶然閱覽『史記』,見有不少的古代民族神話。擴大探究,從不同的民族神話而知各民族的動向,及民族的文化特色。費了一年多時間,寫了這部書;意外的身體也好轉,體重增加到五十公斤了!
六十五年(七十一歲):我覺到身體衰老,對從前要將『印度之佛教』,分別寫成多部的理想,已不可能實現。所以選擇重要的,從部派而發展到大乘佛教的過程,與初期大乘多樣性而趣入佛道的一貫 [P165] 理念,去年來開始作一重點的論究。
六十九年(七十五歲):三月底,『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八十多萬字的寫作,時寫時輟,經五年而完成。論究的問題不少,資料又繁多,這部書不免疏略。然大乘菩薩道,有重信的方便易行道,有重智慧或重悲願的難行道,而從「佛法」發展到「大乘佛法」,主要的動力,「是佛涅槃以後,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以自己探究所得的,「為佛教思想發展史的研究者,提貢一主要的線索」。本書出版後,評介者有楊惠南與萬榮勳居士。
七十年(七十六歲):四月底,『如來藏之研究』脫稿。這是重在如來藏、我、佛性、自性清淨心──真常論的早期思想;融攝「唯識」(心)而成「真常唯心」,還沒有多說。七月,寫了『論三諦三智與賴耶通真妄』──讀『佛性與般若』,這是對牟宗三的著作,引用我的意見而又不表同意所作的辯正。
七十一年(七十七歲):七月初,『雜阿含經論會編』完成。呂澂的『雜阿含經刊定記』,早已指出:『瑜伽師地論』「攝事分」(除律的「本母」),是 [P166] 『雜阿含經』的本母,但內容過於疏略。我在『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明確的對比排列,但還小有錯誤(現已改正)。所以重新論定,斷定『雜阿含經』缺少的兩卷,原文是什麼。將『雜阿台經』的「修多羅」部分,與論文並列。經文的「祇夜」、「記說」部分,也一併排列;並附入我的『雜阿含經部類之整編』於前。在比對配合等過程中,心如等給以很大的幫助。日本名學者水野弘元評論為:「印順法師說之『雜阿含經』一文,不論就其組織型態,乃至其復原層面,都是極其合理的!其評審、確實及其整合等點,都遠遠超逾於日本學者的論說」(關世謙譯『雜阿含經之研究與出版』)。
七十三年(七十九歲):九月初,三萬餘字的『遊心法海六十年』脫稿,敘述自己的學思歷程與寫作。十二月,『空之探究』脫搞,從佛法、部派、般若經,到龍樹論而完成緣起法即空(性)即假(名)的中道。
七十四年(八十歲):三十一年所寫的『印度之佛教』,我想分別的寫成多少部,所以沒有再版,台灣也就少有人知道這部書。『妙雲集』出版以後,知道 [P167] 的人多了,抄寫的,複印的,私下出版的,看來這部書終究非出版不可。五月裡,我把這部書,修正文字,改善表式,有些錯誤而應該修正的,附注參閱我所作的某書某章某節。這樣,我又寫了一篇『印度之佛教重版後記』。
「佛涅槃後,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是佛法發展演化中的主要動力。在發展中,為了適應信增上人(也適應印度神教),施設異方便,對佛法的普及民間,是有功績的。但引起的副作用,使佛法演化為「天(神)佛一如」,迷失了佛法不共神教的特色。為了思想上的澄清,八月起,著手於『方便之道』的寫作,已寫了「佛法」、「大乘佛法」部分,約十五萬字。由於體力日衰,想到應該先寫的,就停止下來。
七十五年(八十一歲):一生的寫作,感覺到對佛教沒有什麼影響,當然也多少有人贊同,有人批評。所以搜集起來,編為『法海微波』,作為一生的紀念文章。
七十六年(八十二歲):我對印度佛教,已寫了不少,「但印度佛教演變的 [P168] 某些關鍵問題,沒有能作綜合聯貫的說明,總覺 得心願未了」,所以去年秋季以來,即開始『印度佛教思想史』的寫作,到今年七月中旬才完成,約二十七萬字。
七十七年(八十三歲):七、八月間,忽從一個「心」字中,發見、貫通了印度佛教史上的一個大問題,也就扼要的寫出了(三萬多字)『修定──修心與唯心‧祕密乘』。
七十八年(八十四歲):我的著作太多,涉及的範圍太廣,所以讀者每不能知道我的核心思想。因此,三月中開始寫了『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三萬字),簡要的從「印度佛教嬗變歷程」,說明「對佛教思想的判攝準則」,而表示「人間佛教」的意義。夏、秋間,又寫了『讀大藏經雜記』,『中國佛教瑣談』。 [P169] 八十年(八十六歲):『大智度論』是龍樹所造,鳩摩羅什所譯,這是中國漢譯保有的大論,也是我「推重龍樹,會通阿含」的重要依據。近年來知道外國學者,有否認是龍樹造的,或想像為羅什附加了不少。只是身體衰弱,不能長篇寫作,引為遺憾。暑假期中,得到昭慧同學的贊助,我才搜集資料,分別章節,口述大要,由他筆記整理成大約六萬字的『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並於「東方宗教研討會」上發表。
八十一年(八十七歲):寫了『「印順法師對大乘起源的思考」讀後』。這是對「在家主體」意識者誤解我的意見而寫的評論。
八十二年(八十八歲):寫了『大乘起信論與扶南佛教』,『「我有明珠一顆」讀後』。
八十三年(八十九歲):自傳式的『平凡的一生』,是六十年夏天寫的,到現在已二十多年。在這二十年中,雖說沒有什麼可寫的,但到底過了這麼久的歲月,也有多少可寫的。所以去年臘月起,雖大病出院不久,對舊作作了補充,或 [P170] 時日的修正,另成一部『平凡的一生(增訂本)』(編入『妙雲集』下編十『華雨香雲』的『平凡的一生』,照舊不改動)。
我的寫作,就是這一些了。寫作的動機,雖主要是:「願意理解教理,對佛法思想(界)起一點澄清作用」;從『妙雲集』出版以來,也受到佛教界的多少注意。然我從經論所得來的佛法,純正平實,從利他中完成自利的菩薩行,是糾正鬼化、神化的『人間佛教』。這一理念,在傳統的現實而功利的人心,似乎是撒種在沙石中,很難見茁壯繁盛的!自己的缺少太多(見三十一節),壯年沒有理想,晚年當然也沒有過分的希望,盡自己所能的寫出而已!